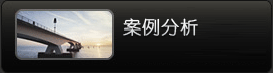- 联系我们
唐山华鑫私家侦探社
电 话 :l53-6950-8649
传 真 :0315-8238l53
地 址 :唐山西外环马驹桥过街人行天桥北行200米
电 话 :l53-6950-8649
传 真 :0315-8238l53
地 址 :唐山西外环马驹桥过街人行天桥北行200米
台湾日治时期刑事侦查与犯罪控制体系研究
1895年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该条约的第二条规定将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划归了日本。自此,日本始领有台湾,台湾地区进入长达50年的日治时期。
日治时期台湾首次适用近代意义上的“刑事诉讼法”,检察官、司法警察、预审法官尚属第一次成为台湾地区的司法概念,从此阶段开始,台湾地区开始了侦查体制近代化的发展趋势。 相对而言,台湾地区的刑事司法近代化过程是缓和的,在西方化的改革中又保留了一些传统特色性质的制度或规则,这一方面是日本统治当局“以华制华”殖民政策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一种适应当时社会治安实际情况的变通。 日治时期长达50年,根据施行法律属性、特征可以大体分为:日本殖民台湾初期,即主要施行殖民地特别法的时期(1895-1922);“内地法延长主义”即以日本内地法为主的时期(1923-1945)。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日治下的台湾逐渐形成了包括军事侦查、一般司法程序、犯罪即决、浮浪者取缔制度、原住民族地区侦查与犯罪控制体制在内的台湾特色的侦查与犯罪控制体系,既带有明显的近代司法体制特征,如建立侦查、检控、审判、执行四大环节,确立预审法官制度等等;又具有日本特色,如强化警察在违法与犯罪控制体系当中的重要角色;此外,保留中国封建时代传统的笞刑,并以此创造了笞刑代替执行自由刑、罚金制度;在原住民族地方还确立了区别于中央山脉以的西汉族区域的原住民治罪体制。 一、西方化的刑事司法制度 (一)军事侦查体制 日本“领台”之后施行军政体制,由日本海军大将担任台湾总督。台湾总督首先颁布了“台湾人民军事犯处分令”,以镇压台湾人的武力反抗。1895年8月6日由陆军省公布“台湾总督府条例”,采用“军事官衙”的组织,在台湾施行军政。此外依据六三法,台湾总督在因地制宜的“特别法制主义”的幌子下集立法、司法、军政大权为一体。[1]同年10月,建立了一个军事法院,审理台湾居民的刑事犯罪及诉讼。随后制定了“台湾住民治罪令”,该法令性质为“刑事诉讼法”,其中虽然采用了西方近代职权机关主动追诉的职权主义机制,由检察官负责侦查。但法令还规定,因“战地”之需要,宪兵将校、守备队长、地方行政首长、警官等非法律专业人员,均可以行使侦查权。而对于政治犯即所谓“国事犯”,根据“匪徒惩戒令”,军队、以及“法定”侦查机关均得以侦查、缉捕甚至直接处以死刑。这样看来,就侦查主体而言,似乎范围过宽,且带有严重的政治威压和军事色彩。 日治下的台湾并未在刑事程序上直接适用日本法。在军政时期,“国事犯”的刑事审判采用一审终审制,并未与殖民宗主国司法机关产生直接关联,在台司法机关听命于总督,自成审级与体系。 (二)西式的犯罪检控机关 日本依大陆法系体制,将台湾司法机关分为“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前者主要负责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及执行,后者则职司审判。1896年5月1日,台湾总督府颁布第1号法律“台湾总督府法院条例”。据此而设立“台湾总督府法院”,自1896年7月15日开始运作。法院采用三级三审制,设有一个高等法院、一个复审法院、十五个地方法院。各法院内设置若干名判官,并以其中一名担任院长,法院配置检察官。台湾总督于1895年军政时期颁定了“台湾住民治罪令”,该法令虽已规定在刑事诉讼程序上由“检察官”(不称为日本法上的“检事”)[2]负责侦查起诉、由“审判官”审理判决,但自1896年前述法院条例施行后,始在法院的组织法上设置“检察官”一职,并由“判官”(不称日本法上的“判事”)职司审判,正式引进东亚传统法制所无的检察官制。[3]一般意义上的刑事案件需经过检察官侦查起诉方可进入到审判程序或者作不起诉处理。检察官可以指挥警察侦查、采取强制措施,也可以自行采取羁押措施。预审法官日本国的《刑事诉讼法》原本师从法国,而后由于引入的欧陆法律与日本社会基础、传统文化“水土不服”,转而学习德国法,所以其“刑事诉讼法”为“德国模式”。但日本在其本国法内保留了原预审法官制度,在1945年前,日本本土以及包括台湾、琉球、伪满洲国等在内的海外附属地均施行了预审法官制度。则专司预审,讯问被告,并可以根据案件罪轻罪重,以秘密方式行使搜查、收集证据之职权。即:检察官、预审法官、警察(司法警察)依据相应的程序法行使侦查权,成为当时的法定侦查主体。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引入职权主义,司法机关依职权主动追诉犯罪行为,所以刑事案件侦查(立案)程序往往是由警察首先发起的。 (三)审检合一体制下的检察官困境 在台湾殖民地,检察官原配置于各法院,二者共事于同一屋檐之下,且检察官附属于法院。自1898年后,始设立“检察局”,由检察官长“指挥监督检察局事务”,检察局与法院虽不相隶属,却均直属于台湾总督。此“直属”是指法院与检察局的“司法行政”事务而言。这项司法行政监督权此处所指司法行政监督权是:审判系统、检察系统均得为“法务部”或“司法部”所“管辖”,此种“管辖”指在管理与行政隶属上的,而并非“司法部”主管具体审判、控诉事权。,即由总督府内“法务部(课)”掌握。 现代法治社会下的司法独立强调对于司法人员身份的超然保障,但日治时期的台湾检察官根本未获特殊的身份保障。1899年台湾总督府以训令发布“台湾总督府法院及检察局事务章程”,其中规定检察官就刑事案件之处理应受检察官长指挥,检察官长就重要案件可自己办理或特别注意之,对于涉嫌刑法“对皇室之罪”、高等官等人员涉及有期徒刑以上刑之案件的起诉与否,均须“具报台湾总督并接受其指挥”。1898年总督府即曾以内训,要求检察官应尽量准予保释和责付,1908年民政长官亦表示司法官应与行政官“相依相扶”,以期司法权行使之圆满。所以说检察官的独立办案权受到极大的限制,其任命、升迁或转所,亦皆操纵于总督之手。 1920年以后,司法独立较前期改善。在考绩及检察官行使职权上给予了一定空间。检察官一方面依旧没有特别身份保障,另一方面就其职务所牵涉攸关统治的思想犯检举部分,总督府对其之控制从未松手。于1940年代初到1945年二战结束,台湾施行“战时特别法”,凡涉及政治刑法的案件,地方法院检察官长须将侦查经过及起诉与否,向总督及“高等法院”检察官长报告并受其指挥。所以,检察官之困境在整个日治时期未得到有效解决,司法独立也无曾实现。 (四)侦查权之立法依据 就日治时期的侦查权行使依据——刑事程序法而言,首先施行的是1895年的“台湾住民治罪令”。其后是1898年7月的“律令”第八号:在确定刑事事项适用日本《刑事诉讼法》的同时,规定日治下的台湾人及中国大陆人,仍然依照“现行之例”即“治罪令”。直到1908年,台湾总督才颁布“台湾刑事令”,规定:在保留“台湾刑事诉讼特别法”的同时施用近代化的日本“1890年刑事诉讼法”。在之后的1924年,台湾始施行了日本“1922年刑事诉讼法”,同时保留了原“有关施行于台湾之法律特例”中的刑事内容。 二、旧有犯罪控制体制的延续 所谓旧有犯罪控制体系是指保甲制度以及鞭笞刑等中国封建时代的犯罪控制以及违法行为惩戒措施。 (一)保甲制度 保甲是中国封建统治镇压人民反抗的传统制度,日治时期的台湾沿用了这一“惯例”。1896年,日本统治当局即利用户口调查的契机,以宪兵及警察为调查机构,将台湾西部平原的汉族住民加以调查、并制作户口调查簿。此后的1905年,依据“临时台湾调查规则”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户口调查,随后出台以防止“民变”为目的的“关于人口异动之申报规则”。儿玉后藤成为台湾总督后,进行了所谓“台湾住民组织化建设”,于1898年公布“保甲条例”,最终以此为依据形成了“保甲制度”。保甲目的在于维持社会治安,防止民众反对当局殖民统治。具体而言,以户为单位,将每10户为一单位组成一甲,由10甲组成一保,保甲内住户承担连带责任。与保甲制度相关联的,在保甲内设立壮丁团,维持保甲内秩序。“保甲制度”的实施,一方面与当时的社会治安状况和犯罪情况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也是日本当局对刚刚平息的抗日活动进一步打压的举措。在由一定数量台湾人居住的“社区”设立一甲,家长直接对“专管警察”(即以一定居民点为单位设置的一名专属责任区警察)负责,充当警察的耳目,同时还兼具纠举、协助缉拿罪犯的职责,当然其自身往往承担着“告密”不利的种种不利后果。 (二)鞭笞刑 鉴于日治初期的犯罪形势,台湾总督恢复了清朝及以前的鞭笞刑,于1904年制定“罚金及笞刑处分例”:1.主刑应处以3个月以下重禁锢;2.主刑或从刑应科以100元以下罚金,且在台无一定住所或无资产者;3.应处以拘留或科料(金额较少之罚金),得将其宣告刑换成笞刑;上述1之情形,亦得以换刑为罚金。[4]值得注意的是,该条例只适用于台湾中国人以及所谓“清国人”,并不对居住于台湾的日本人或他国人适用。此类 “刑罚”本身就带有行政处罚的意味,这与日本当时的法制状况是有关联的。当时的日本本土对于违法与犯罪的概念尚有一定认识上的不一致,并且在官方(或称刑事司法上)将依现代法治认为是违法的行为并入到犯罪行为当中去了。在这种制度下,罚金、笞刑、剥夺自由刑(拘留)得以在一定程度内互换,尤其是当罚金执行不利的情形下,笞刑往往成为首选。这样一来,在减少监狱在押人员的同时,也降低了警察任务量,通过一次性的惩罚即笞刑而免除了其他刑罚相对独立的执行程序。 三、特别法视野下的刑事政策 (一)强制措施“简易适用”的制度 日治时期台湾地区侦查机关过度扩张的侦查权主要源于所谓“台湾特别法”。根据1899年“律令”第九号,检察官可以迳行请求预审,即对一定范围的案件,检察官可以直接行使本来应当由预审法官行使的预审权(即中国大陆之侦查讯问),这就导致了台湾在预审权归属方面不同于其宗主国,《日本刑事诉讼法典》乃是有保留地施用于台湾。其次,根据上文提到的“关于刑事诉讼手续之律令”:检察官可以对非现行犯,认为有紧急处分之必要时拘提犯罪嫌疑人,进行搜查、扣押以及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等强制处分权,进而实际履行了根据日本“刑诉法”应属法官的职责。1904年3月制定了新的“犯罪即决例”,赋予了地方长官以犯罪即决权。随后出台“刑事诉讼特别手续”将上述两个法令合二为一,大大强化了检察官、法官、警察在侦查程序中的权力。即便在1924年施行日本“1922年刑事诉讼法”以后,也特意设立了第三章——有关刑事之特例。除了将之前施行的以“令”的形式通行的“特别法”加以法律上的肯定,同时继续扩大了侦查权,加入现行犯及“急要案件”部分。同时,对于在台湾无固定居所、有逃跑及毁灭证据可能的犯罪嫌疑人,如果情况紧迫,检察官可以无拘票迳行采取搜查、扣押、勘验、讯问等侦查措施;司法警察官也享有较长的讯问羁押(拘留)期限。这样宽松的刑事强制措施发起程序,无疑助长了东亚传统的警察刑讯文化。1905年的“刑事诉讼特别手续”第12条特别规定,应处以主刑1年以下剥夺自由刑或200元以下罚金之案件,于检察官及民事原告无异议时,法院得不再为其他证据之调查[5]。也就是说,当时的法律以明文形式将口供作为可以独立定罪结案的唯一证据,这样一来,刑讯逼供就当然地大行其道。此外,日本自身就崇尚警察政治,而台湾作为其殖民地存在,为了维护政治统治,统治当局更加专注于警察建设,促使刑讯逼供致伤(死)案件屡屡发生。 直至1945年,台湾地区侦查机关的权力空前扩张,违背了近代刑事诉讼法的程序正义,且对人权的侵犯极为严重,阻碍了侦查体制的进一步发展。 (二)刑事案件即决制度 犯罪即决制度指,警察署长及分署长或其代理官吏,以及宪兵队长及下士在其辖区内,在听取被告人陈述并调查证据后即为宣判,惟对于判决需向地方法院请求为正式的裁判。[5]214其渊源在于1896年台湾总督颁行的“该当于拘留或罚金之刑的犯罪即决例”,根据该条例规定:“对于应当处以10日内拘留的违法行为,由警察长官、宪兵队长自行裁决。”[6]后来逐渐演化为犯罪即决制度,是日本国内警察政治在台湾岛的“延长”适用。当然,警察(或即决官)有权即决之违法行为是根据政令变化而变化的,其范围因日本殖民需要而膨胀。作为钳制机制,形成了相应的移送程序,即有权即决的官员受理刑事案件以后,如果认为嫌疑人所涉罪名或应受的刑罚超出职权范围,应将案件移送检察官侦查。同时,嫌疑人也享有异议权,可以申请转为一般案件侦查、进而进入普通司法程序。使得非即决案件可以上升为一般司法程序进而得以得到中立裁判。而实际上,警察及行政官员、宪兵在即决程序当中,往往不会给予转为普通程序的机会,进而实质上剥夺了检察官以及预审法官的侦查权,在“初查”或侦查阶段即截留大量刑事案件,使得犯罪即决成为轻度犯罪的“前置程序”,大大破坏了司法体制的完整性。 (三)浮浪者取缔制度 此外,根据台湾总督府1906年制定的“台湾浮浪者取缔规则”,无固定居所、职业,有妨害公安、扰乱风俗之虞者,予以“戒告”[7],仍无改变则被送往固定处所强制就业。所谓开垦实际上就是将“可能犯罪的”无业人员(包括了大量政治犯)送到“浮浪者收容所”,参加农业劳动,其惩戒方式为强制劳动。类似于大陆地区20世纪50年代盛行的劳动教养制度,实际上是对于没有达到犯罪程度的人处以剥夺自由的刑罚。这种情况下,由地方官、厅首长、警察官行使侦查职权,直至最后由台湾总督许可执行。从而,行政警察实际上依法得以在司法程序当中掌握侦查权以及刑事执行权。导致刑罚权主体“非司法化”的独特现象发生。 (四)原住民族地区的侦查与犯罪控制体制 日本统治者控制下的台湾最高行政机构——台湾总督府一开始就未对中央山脉及台东地区等原住民族区域施行近代化的刑事司法体制。一方面由于台湾总督府统治初期,对于被称为“生番”的高山族、泰雅族等原住民族缺乏实质控制。另一方面,日本当局亦存在制度“因情势而变通”的考虑。所以,对于原住民族是否应受刑事追究经由专责处理“番务”的开垦署长随即处分,而少数民族为主体的“社”所施行的是近代司法体系下的侦查制度。在1903年后,统治当局最终确定由警察系统来处理高山族等原住民族的法律事务。这里的警察系统一方面担当侦查机关,同时也作为“法律事务官”存在。对于重大案件,例如强盗杀人案件,可移送检察官侦办[8]。也就是说依据当时法令在一定范围内,刑事案件由警察(行政警察)直接侦办,而对于违反台湾总督以“令”或“敕”的形式施用于台湾的日本刑法所规定的严重犯罪案件(指危害日本统治或侵犯生命权的刑事案件)则由行政警察“初查”后移交检察官、司法警察侦查。这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双轨侦查体制,即一定范围内在原住民族聚居的“社”内侦查,并裁决;重罪则进入普遍施行的刑事法律与刑事程序法进行侦查。就移送的前置条件而言,需经过台湾总督府之指示。总督府作为全台湾最高统治机关,自然不可能常务性地审批刑事案件的移送事项,这也导致了大量非重大刑事案件实际上由警察侦查并处断,实乃警察侦查权力之扩张。值得一提的是,在警察行使侦查、司法裁决权力的同时,也常常邀请少数民族内的首领参与“刑事诉讼”当中,并将一定的民族“习惯法”或者说所谓“旧惯”(指日本占领之前台湾业已存续的法律习惯)带入侦查程序当中。最终使得原住民族地区形成了带有风格独特的侦查与犯罪控制体制。 四、结语 日治时期的犯罪控制体系由警察作为发起者,对于属于自决案件的范围则即决之;可以适用“浮浪者取缔制度”的无业者亦由警察“取缔”之;至于无法自由裁量的刑事案件,则由警察移送检察院进入一般司法程序;此外,原住民地区还适用原住民治罪体制,如果案件重大就可能转为一般司法程序。这样一来,一部分犯罪行为实际上是由警察来处断的。警察权的膨胀,压抑了司法权的行使,进入控诉、审判环节的案件大大减少。如果把犯罪案件比作一个金字塔,犯罪即决案件的数量就如同金字塔的底端,浮浪者取缔案件与军事检察案件、原住民治罪案件共同构成次底端,而司法审判案件却成了顶端。进而,形成了日治时期的台湾特色侦查与犯罪控制体系。 |